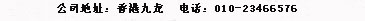在个人所得税中,是否存在费用扣除不完善的
个人所得税本质是对纳税人的“净收入”进行征税,在税法中体现为扣除各项费用后的应税额。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所遵循的法律价值来源于宪法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以及“量能课税”的税收基本原则,其本质是对纳税人“生存权”的保障,是影响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的核心要素。
因此,费用扣除设计的落脚点应当是保障纳税人维持个人及其家庭最基本的生活和发展需要,即“基本生活费用不课税”,这一原则被学术界广泛认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综合所得规定的费用扣除包括:基本费用扣除、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其他扣除。
其中基本费用扣除标准为每年元(每月元),相较于之前每月元的标准有较大提高,有效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此外,年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新增了涉及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四个方面的六项专项附加扣除,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量能课税原则。但是从公平的角度出发,仍存在部分问题有待完善。
未考虑地区经济水平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各省份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更是存在较大差距,且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较大。显而易见,在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地区或城镇的纳税人,维持个人及其家庭最基本的生活和发展所需要的成本,明显高于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或农村地区。
首先,全国统一采用每年元的综合所得基本费用扣除标准未考虑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虽然,全国适用统一的基本费用扣除标准便于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工作的进行,也体现了形式上的公平。
但在经济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存在差别的地区实行统一数额的基本费用扣除标准,掩盖了区域差异性,违背了税收的实质公平原则。这样的扣除标准,对于中西部经济落后的地区或农村居民而言也许是合理甚至绰绰有余的,但是,对于像北上广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的中低收入群体而言,面对较高的生活成本,这样的费用扣除标准不能有效地缓解其生存压力。
全国采用统一的费用扣除标准缺乏个性化调整,不能体现地区和城乡的差异性,不符合量能课税和税收公平原则,影响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实现。其次,专项附加扣除中子女教育扣除标准未考虑地区差异。
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光造成了地区之间教育质量的差异,更造成了教育成本的差异。《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第五条对子女教育一项规定:“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和学前教育的相关支出,扣除标准为每个子女每月元。”
以处于大学教育阶段的纳税人子女为例,其在校生活费用和学费均来自父母,而在经济发达地区上大学的子女和在经济落后地区上大学的子女的这两项花费是存在明显差距的,但是,子女在同一地区上大学的纳税人可能来自不同的地区。
这就造成了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去经济落后地区上大学,由于其父母收入较高,支出的子女教育费用负担较轻;而来自经济落后地区的学生去经济发达地区上大学,其父母收入一般较低,支出的子女教育费用负担较重。
值得注意的是,专项附加扣除中对于住房租金这一项却考虑了地区差异,根据城市行政级别和城市人口规模的差异划定了不同的扣除标准。但是,专项附加扣除中关于子女教育的扣除标准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中纵向公平的要求。
缺乏扣除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过去的20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保持高位运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多的同时物价水平更是大幅上涨,我国处于持续的通货膨胀之中。
然而,我国个人所得税自设立以来就采用固定的费用扣除标准,并未设立与经济运行形势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虽然采取固定的费用扣除标准操作简便高效,但是缺乏弹性,在出现通货膨胀时不能与收入变化、物价波动等动态经济因素相适应。
当通货膨胀发生时,纳税人的名义收入上升,但是在此情形下物价水平上升速度往往会超过收入的增长幅度,使得纳税人的购买力下降,纳税人的实际收入却是减少的。在此情形下,因为没有费用扣除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扣除额会缩水,纳税人在扣除固定费用后的所得额可能会适用较高的税率,使得纳税人实际上承担比原本更重的税收负担。
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三项重要指标有CPI(消费者物价指数)、PPI(生产者物价指数)以及国民生产总值价格折算指数,其中比较重要的是CPI,它反映了特定时段内一般居民家庭所购买的消费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水平变动情况。
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并未与CPI关联以形成动态的调整机制,在物价水平持续上升的背景下,设立费用扣除标准指数化的动态调整机制十分必要。尽管,我国之前几次的个人所得税调整都以经济指数为依据对费用扣除额进行了调整,但是随着物价的快速上涨,调整也愈发频繁。
在我国,工薪阶层是个人所得税的主要负担者,间歇性的调整扣除额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不设立费用扣除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难以使扣除额具有时效性,也难以保障广大工薪阶层的基本生计需求,不利于税收公平的实现。
未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家庭因素
年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后新增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赡养老人、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大病医疗六项专项附加扣除,可以看出我国逐步将家庭因素纳入征税的考量范围。但是,目前个人所得税法中对于专项附加扣除的规定尚不完善,考虑到的家庭因素的扣除部分还不够充分,个别条文内容更是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讨论。
首先,专项附加扣除中对赡养老人的规定考虑不充分。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负担是当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压力。虽然《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和二十三条中根据纳税人是否为独生子女和被赡养老人是否年满60岁规定了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
但是,每个家庭,每个纳税人所承担的养老负担却是不同的。在我国,部分老人有养老金或退休金,甚至是高额的养老金或退休金,而部分老人甚至没有养老金或退休金,这就造成了不同的纳税人需要承担不同的养老压力。
尤其是在我国农村地区,多数老人普遍没有养老金或只有很低的养老金。而在城市生活的老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企事业、机关单位的退休职工,他们有较高的养老金和退休金。这部分老人无论是身体状况还是经济状况都普遍好于农村老人,甚至可以在经济上补贴子女。
而部分无养老金和退休金的老人在不到60岁时可能已经不具备取得收入的能力了,这部分老人的子女作为纳税人需承担更大的赡养压力,在当前的费用扣除标准下与拥有养老金和退休金的老人的子女相比显然是不公平的。
此外,专项附加扣除大病医疗一项未将纳税人的父母一方发生的医药费用纳入扣除范围。《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本人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以选择本人或其配偶扣除;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选择由其父母一方扣除”。
而对于纳税人年满60岁以上的父母发生的大病医疗支出,当前个人所得税法并未做相关规定,在实践中也不能扣除。在税收实践中,除部分有积蓄的老人外,多数老人的医疗费用是由子女来承担的。
年满60岁的被赡养老人与纳税人的未成年子女相比,因身体机能因素更容易生病,一旦生了大病更是需花费高额医药费,如果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其家庭甚至可能因病返贫。当前个人所得税将纳税人年满60岁以上的父母的大病医疗支出排除在扣除范围之外是不合理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pingguoxiu.net/xhblzl/9833.html